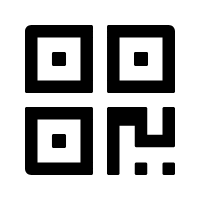历史教学中应注重史料的渗透
“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读历史,每次读了之后,没过多久就忘了……还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材料题,我好怕做材料题,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答,该答什么,我该怎样才能学好呢?”
“每次一做材料题就没话可说,不懂得分析材料,直接导致材料题失分严重。……每次碰到不会做的材料题时心里就很烦,总是会说‘哎!随便写点,反正也想不到。’”
“这次考试我主要败在了材料题,不知道怎么我就是对材料题有点恐惧,……碰到材料题时我差不多都会读两遍或两遍以上,但却不知从何下手。”
“简答题的题目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做起来感觉很好,但得分很少,希望老师以后讲练习时,可以多教授一些答题技巧。”
以上文字是来自我所教班级学生对于材料分析题所遇到的困扰。看完之后,我急在心里。我深知材料分析对于学好高中历史是何等的重要,一旦它成为了学生学习历史的软肋,即使你有多能“小打小闹”,等到真正上了战场,那也必将铩羽而归。
学生之所以会在做材料分析题的过程中产生恐惧的心理,甚至是感觉到无从下手,我觉得这跟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有没有注重材料分析能力的培养有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历史学科仅仅被认为是一门描述过去所发生事实的课程,而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已经不可改变,所以学习历史只需要依靠记忆来获得相关知识,比如说简单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影响等,而与思维能力的发展毫不沾边,这种观念显然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正如英国历史教育家汤普森指出“传统的历史教学几乎总是在描述或解说一个认同或确定了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而极少深入运用各类资料。在这种传统模式中,我们知道的历史是理所当然的,而至于我们怎样知道历史,则是学校历史教学中忽视的问题。”这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历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很难做到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或者是有充足的材料依据去思考。为了尽量的避免史实的罗列和结论的简单得出,我都会做一些背景和材料的铺陈,然后尽可能的去帮学生分析,但这也许就是问题的所在:一切都是我在分析而已,学生并没有真正加入进来,他们只是沿着我的思维,迷迷糊糊,不知所以然的在接听,然后真正应该学会分析的主体却仍然摸不着方法。学生甚至已经懒得去追问“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反正老师老师会帮我们分析,最后也必然会把自己的分析成果形成文字让我们记录下来。这样一种惰性,只会让学生暂时接收的知识在容器中腐烂变质,根本无法转化成自我的理性认识。这样一种被知识奴役的处境,试问学生又何来的勇气去分析历史,鉴赏历史,发现历史呢?
如何消除学生的恐惧和茫然,才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在新课程理念下,更加注重学生获取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强调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史料的运用方式似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处理史料的方法大致有:
(1)展开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提问形式是“在这段资料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
(2)鼓励学生去分析史料的内容,从中引出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只是去重复或摘要史料的内容。
(3)时常要求学生针对不同材料的证据,就内容和可信度作比较。
(4)明确针对相互冲突的证据进行讨论。
(5)对同一事件之不同的历史论述加以比较。
(6)选出一个主题,给予学生多段来源不同的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对照整理,并且解释其中的差异,进而形成他们自己的推演,找出自己的结论。
(7)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眼光去找出史料中带来的问题,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
也就是说,教师在运用史料时,不能只是为了证明观点或者是说明结论,而应该拓展史料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史料锻炼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功能,让学生在分析运用史料时体验亲自获得知识的感受,如此一来,史料的深层次利用容易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从而使知识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当然,教师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要注意学生的知识背景,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曾指出:“如果我不得不将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当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去进行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在运用史料时应该首先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层次。否则的话,太简单无法开动学生的脑力劳动,学生几乎不需要进行相应的思考和探究;太难超出学生能力水平的话,学生无法沿着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思考,这样反而增加学生分析史料的压力,从而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恐惧和排斥,也就更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在给学生提供具体的史料进行教学时,应该先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确保史料的分析能有一个广阔的视野。
我想,只要我们的教学多一份细心与责任,永远怀着一颗不断积累与学习的心,学生的恐惧与茫然终将被自信的笑容所驱散。(历史组 凌旸)
“每次一做材料题就没话可说,不懂得分析材料,直接导致材料题失分严重。……每次碰到不会做的材料题时心里就很烦,总是会说‘哎!随便写点,反正也想不到。’”
“这次考试我主要败在了材料题,不知道怎么我就是对材料题有点恐惧,……碰到材料题时我差不多都会读两遍或两遍以上,但却不知从何下手。”
“简答题的题目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做起来感觉很好,但得分很少,希望老师以后讲练习时,可以多教授一些答题技巧。”
以上文字是来自我所教班级学生对于材料分析题所遇到的困扰。看完之后,我急在心里。我深知材料分析对于学好高中历史是何等的重要,一旦它成为了学生学习历史的软肋,即使你有多能“小打小闹”,等到真正上了战场,那也必将铩羽而归。
学生之所以会在做材料分析题的过程中产生恐惧的心理,甚至是感觉到无从下手,我觉得这跟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有没有注重材料分析能力的培养有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历史学科仅仅被认为是一门描述过去所发生事实的课程,而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已经不可改变,所以学习历史只需要依靠记忆来获得相关知识,比如说简单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影响等,而与思维能力的发展毫不沾边,这种观念显然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正如英国历史教育家汤普森指出“传统的历史教学几乎总是在描述或解说一个认同或确定了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而极少深入运用各类资料。在这种传统模式中,我们知道的历史是理所当然的,而至于我们怎样知道历史,则是学校历史教学中忽视的问题。”这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历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很难做到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或者是有充足的材料依据去思考。为了尽量的避免史实的罗列和结论的简单得出,我都会做一些背景和材料的铺陈,然后尽可能的去帮学生分析,但这也许就是问题的所在:一切都是我在分析而已,学生并没有真正加入进来,他们只是沿着我的思维,迷迷糊糊,不知所以然的在接听,然后真正应该学会分析的主体却仍然摸不着方法。学生甚至已经懒得去追问“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反正老师老师会帮我们分析,最后也必然会把自己的分析成果形成文字让我们记录下来。这样一种惰性,只会让学生暂时接收的知识在容器中腐烂变质,根本无法转化成自我的理性认识。这样一种被知识奴役的处境,试问学生又何来的勇气去分析历史,鉴赏历史,发现历史呢?
如何消除学生的恐惧和茫然,才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在新课程理念下,更加注重学生获取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强调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史料的运用方式似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处理史料的方法大致有:
(1)展开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提问形式是“在这段资料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
(2)鼓励学生去分析史料的内容,从中引出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只是去重复或摘要史料的内容。
(3)时常要求学生针对不同材料的证据,就内容和可信度作比较。
(4)明确针对相互冲突的证据进行讨论。
(5)对同一事件之不同的历史论述加以比较。
(6)选出一个主题,给予学生多段来源不同的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对照整理,并且解释其中的差异,进而形成他们自己的推演,找出自己的结论。
(7)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眼光去找出史料中带来的问题,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
也就是说,教师在运用史料时,不能只是为了证明观点或者是说明结论,而应该拓展史料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史料锻炼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功能,让学生在分析运用史料时体验亲自获得知识的感受,如此一来,史料的深层次利用容易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从而使知识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当然,教师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要注意学生的知识背景,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曾指出:“如果我不得不将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当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去进行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在运用史料时应该首先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层次。否则的话,太简单无法开动学生的脑力劳动,学生几乎不需要进行相应的思考和探究;太难超出学生能力水平的话,学生无法沿着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思考,这样反而增加学生分析史料的压力,从而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恐惧和排斥,也就更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在给学生提供具体的史料进行教学时,应该先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确保史料的分析能有一个广阔的视野。
我想,只要我们的教学多一份细心与责任,永远怀着一颗不断积累与学习的心,学生的恐惧与茫然终将被自信的笑容所驱散。(历史组 凌旸)